在往返於大學與部落之間:到處趴趴走的人類學家
邱韻芳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二十三歲決定放棄台大數學系碩士班學業後,人生充滿不可預期的驚喜與挑戰:意外成為暨大人類所兩位創所「元老」之一;擔任暨大原青社指導老師,每年和學生一道大張旗鼓地辦原⺠週;加入芭樂人類學共筆專欄,重拾年少寫作的夢想。2014年,待了十年的人類所被併入東南亞學系,接下原鄉發展原住⺠族專班主任的重責,身邊有了更多的部落孩子一起攜手擴展原勢力,並且繼續期待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好人生。
專注而深情地和她/他的部落發展出⻑期的情誼,這是大家熟悉的人類學家和其研究對象的關係。從這個角度看,我實在是個太過「博愛」且「非典型」的人類學者,收在心頭的部落名字有一⻑串,而且有繼續增加的趨勢。為何如此?這一切要回溯到久遠的那年。
因著無法想像自己未來的模樣,當時碩一的我決定放棄台大數學所的學業轉考人類所。這是我人生中最不順遂的考試連著兩年落榜只能苦苦單戀人類學,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部落在其他場域的美麗相遇[1]。
四年後重回校園,成為人類學學徒。碩論和博論期間,我循著馬凌諾夫斯基的教導,待在一個部落⻑住,和族人一起生活。2004年畢業來到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書後,這樣的模式卻非常嚴重地撞了牆。研究生時,可以很⻑時間窩在部落裡,族人對於「來學習的孩子」非常包容與照顧;進入大學教書後,生活被教學與行政分割,能自在和族人相處的時間零碎不易建立關係,「大學教授」的頭銜又不時面臨「期待」(「你能給部落什麼?」)或「質疑」(「又是個要到部落拿原住⺠文化換學術成就的人?」)的眼光。無法回饋部落的焦慮,加上對自身各種能力的懷疑,導致有好一段時間我幾乎無法跨進部落......
近幾年來,我和部落的關係不只「回溫」還更「熱絡」了起來,而且是忽南忽北地到處趴趴走。從踟躕不前到再積極躍入,之所以有如此神奇的轉變主要歸功於兩件事--和原住⺠青年的相遇,以及參與了原住⺠族委員會(簡稱「原⺠會」)的部落總體營造計畫。
一起「部落」一起「青春」:從原青社到原專班
2007�年底,暨大成立了「原住⺠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由人類所潘英海所⻑擔任中心主任,我無從推託地義務協助中心的業務與計畫,卻沒料到因此開啟了和原住⺠社會接觸的另一扇門。
暨大雖然緊鄰信義與仁愛兩個原住⺠鄉,但當時校園內看不到任何原住⺠議題,也沒有原住⺠學生社團。為了改變這個「奇怪」的現象,和潘老師商量後,2009年由我和當時的中心助理吉渥絲負責,找來校內原住⺠學生工讀協助,舉辦了盛大的原住⺠週。我們在大雨中運來了美麗的達悟族十四人大船佇立在校園,加上特地從蘭嶼運來各種相關素材,舉辦了蘭嶼拼版舟巡迴展;邀請和平國小的泰雅族師生將他們的原⺠風陶藝作品來展覽;請到數位導演現身說法,分享他們所拍攝的原⺠紀錄片;以及與暨大學生會合作,舉辦有烤豬、在地原⺠樂團,和原住⺠明星的大型戶外晚會。如此地勞師動眾,一方面是希望一舉在暨大打響原住⺠議題,另一方面企盼能藉此刺激無聲「潛藏」在各系的原住⺠學生起身做些什麼。
我們的努力有了最直接真誠的回報,活動結束後,參與的原住⺠學生熱情澎湃地在慶功宴上決定成立Knbiyax Club(暨大原青社[2],並邀請我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自此我和Knbiyax每年大張旗鼓地籌畫、宣傳、舉辦原⺠週,它是我們向心力和情感凝聚的場域,支撐起一個不到十人的小社團散發驚人熱力,使其成為暨大一個很特別的傳統延續至今。
記得Knbiyax成立之初,無論社課或原⺠週,學生重心多放在歌舞練習上,我雖不盡然贊同卻未出聲,只是很「計謀」地透過每年原⺠週必有的紀錄片暨導演映後座談,或演講、部落產業工作坊等各種「策略」,帶入原住⺠社會文化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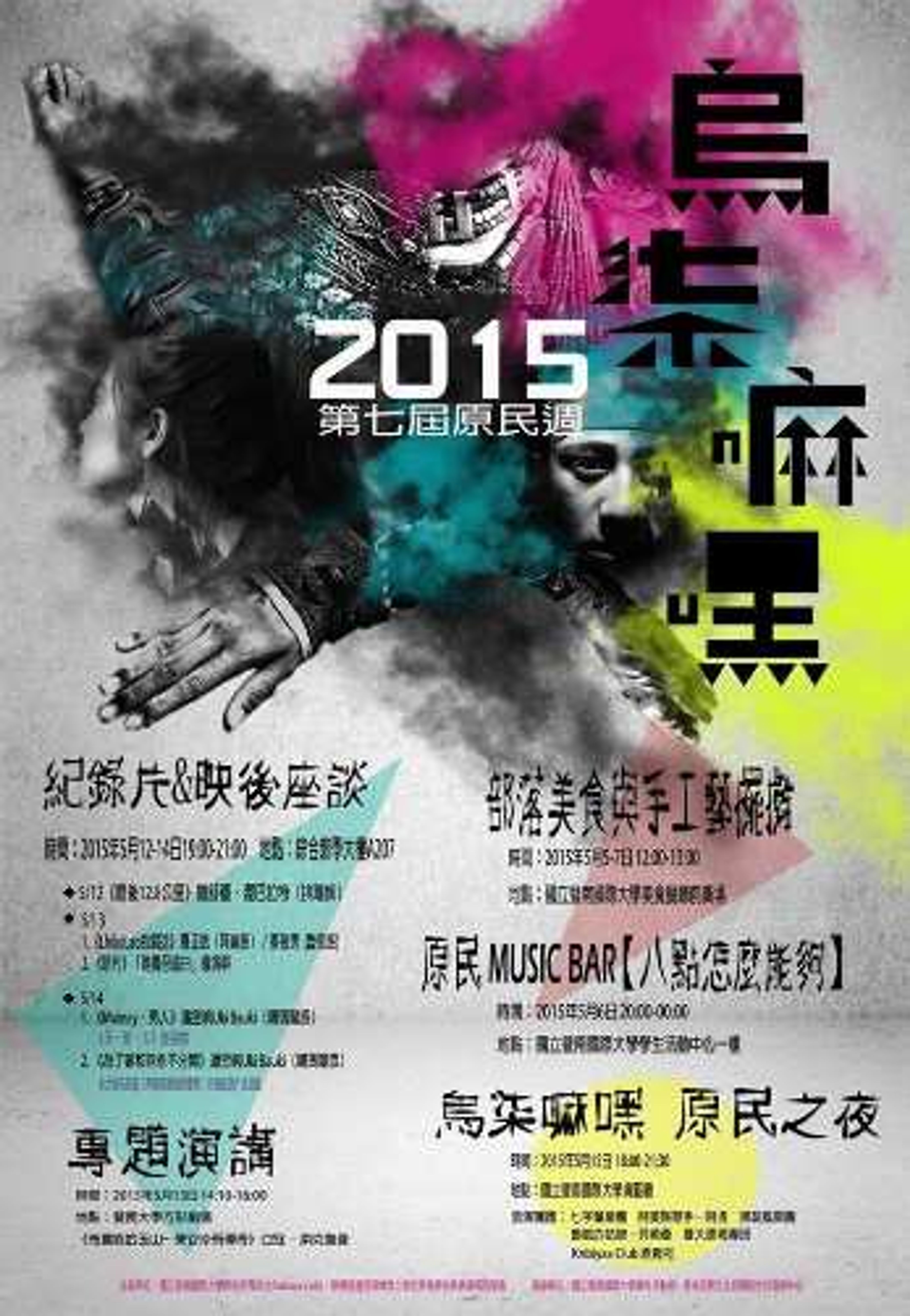
第七屆原⺠週海報

第七屆原⺠週邀請卡,由學生自己攝影取景、當麻豆。
原⺠週之外的學期中或暑假,我帶著Knbiyax南下觀賞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了你》的戶外演出、參與古華排灣族收穫祭、吉貝耍⻄拉雅夜祭;北上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看都蘭特展;往東到奇美部落「文化泛舟」、參加豐年祭;以及連著兩回,大陣仗地揪團到都蘭阿米斯音樂節玩耍。透過這些跑很遠的「社遊」,希望讓我的Knbiyax們有更多親近「文化」、思想「文化」、討論「文化」的機會。但其實收穫最多的是我,因為這並非單向的帶領或付出,而是一個互相陪伴與彼此培力的過程。過去習慣一個人闖蕩的我,突然有了一群可以一起跑部落、談部落的夥伴。和這些年輕原住⺠孩��子相處的過程中,我逐漸知曉了他們與部落的關連或斷裂,他们對「文化」的熱情、迷惘或陌生。一頁頁閱讀這些年輕的「生命史」並走入其中,不僅滋養了我的人生,彌補了過去我理解原住⺠社會時很大的一塊空缺,也幫助我更能理解和掌握當代的部落變遷。
和Knbiyax一起「部落」一起「青春」的美好學習歷程,重燃了我當年初識部落時的熱情,也大大提升了我的戰鬥指數。因為經過了這樣的「培訓」,我方能有勇氣和後盾「膽敢」在2014年接下暨大新成立的「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族專班」主任一職。這回不只是社團,而是一個系的規模,不只是辦活動,而是要用極有限的人力和資源變出一套可以養成返鄉部落青年的四年課程。
如何設計出以原住⺠社會文化為基底,又能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專業課程?這是個持續建構中的巨大工程,但我確知的是一般的教室上課模式不足以因應,因此我和專班的同事們每學期安排多場與原住⺠傳統或當代議題相關的演講、工作坊,學期中帶學生到部落參訪,暑假到部落出隊帶兒童營、製作部落地圖。此外,我們還請來部落的族人帶著學生在暨大種小米、蓋穀倉、竹屋,作傳統美食,製作漂流木椅,並經學生票選把這塊園區霸氣地命名為「原住⺠保留地」。[3]
無論是課程或活動,若想達成專班名稱--「原鄉發展」--的理想,我必須不斷汲取來自部落的養分,才能掌握當代原住⺠社會的多元和動態,以免傳達給學生僵化的文化意象。然而,這僅僅依靠人類學的知識、文獻絕對是不夠的,所幸,這些年來在與原住⺠青年「搏感情」��的同時,我也跨出校園,參與了原住⺠的部落總體營造計畫。

2016 年 10 月,和 Knbiyax 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看都蘭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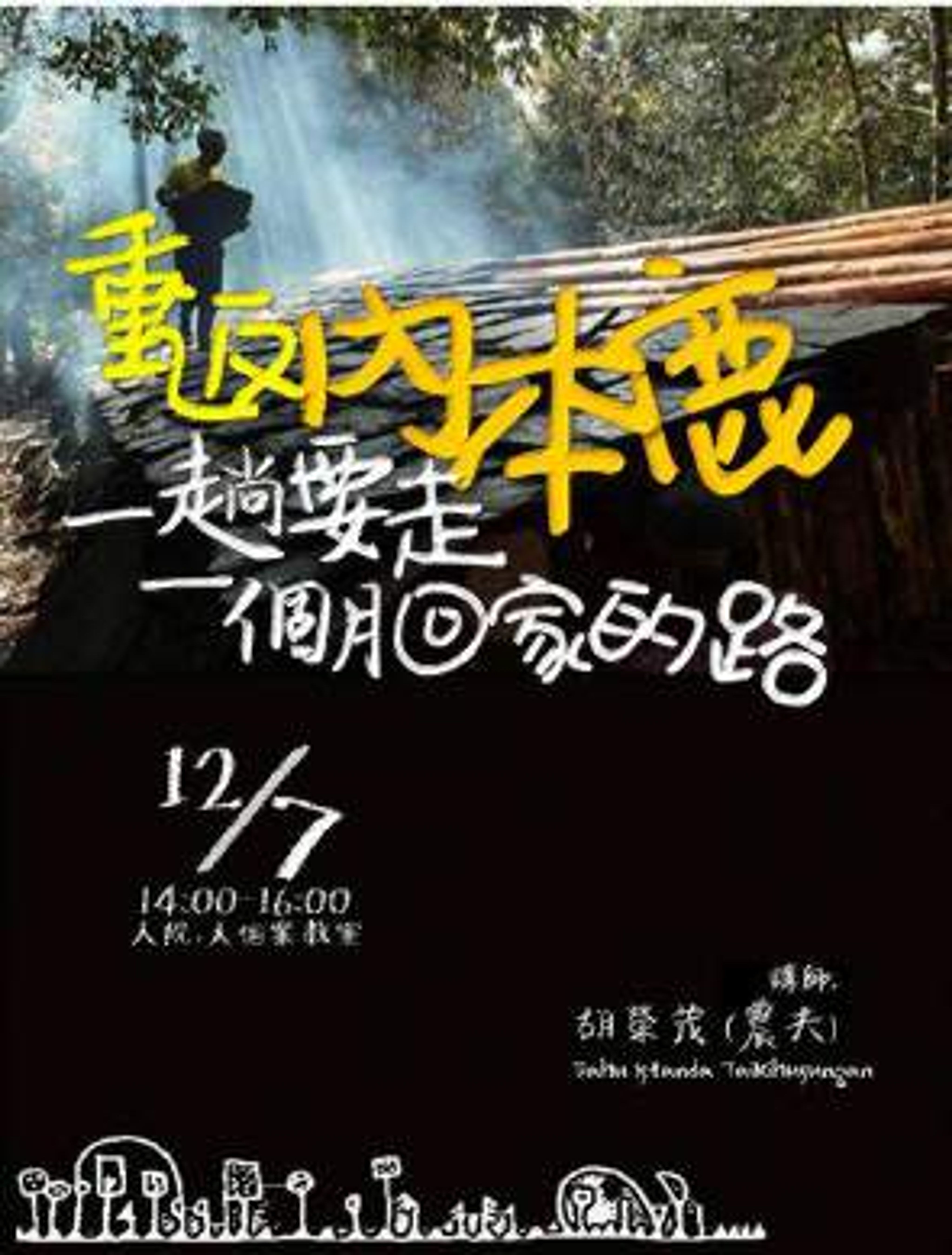
精美的原專班演講海報之一

2016 年暑假,帶原專班學生至都達部落作部落地圖

2015 年 5 月,在暨大舉行小米收穫與穀倉落成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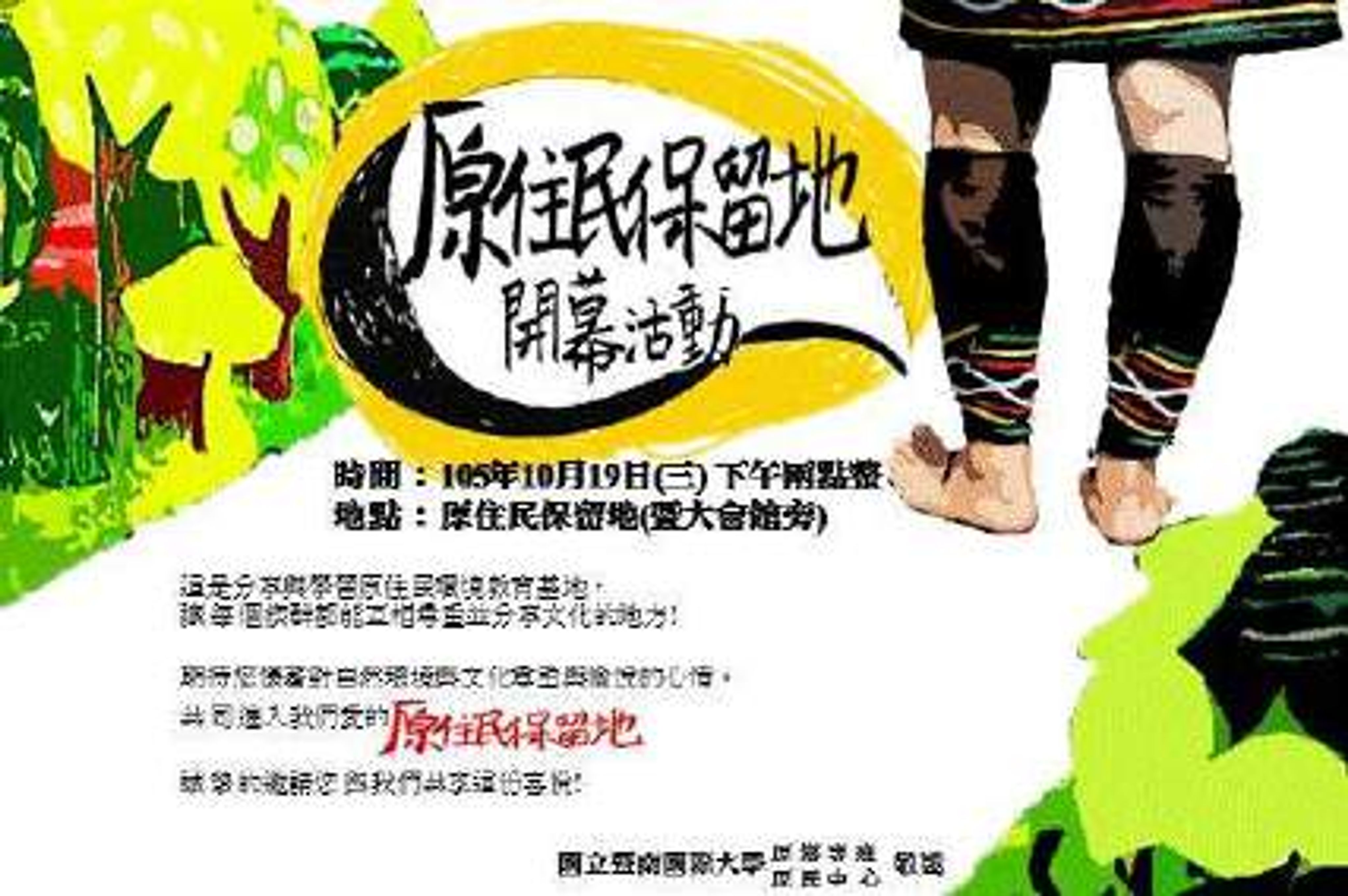
「原住⺠保留地」開幕活動邀請卡
「發展計畫」中的人類學家
2005年,原⺠會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行「原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歷經「重點部落」、「示範部落」、「永續部落」與「活力部落」等名稱的更迭,在同樣的精神與脈絡下執行至今已邁過十年的門檻。2009年,有多年部落經驗的埔里在地NGO團體「台灣原住⺠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首次承接此計畫之全國專管中心與北區輔導團隊的工作,秘書⻑惠雯邀請我擔任評鑑委員,而後幾年隨著與原促會關係日深,我參與這個計畫的面向也越來越廣。
加入計畫跟著原促會四處跑部落後,讓我對於當代台灣的「部落發展」現象有了比較具體的瞭解。然而,作為喜好從閒聊中獲得「文化」,一進部落就想黏著不走的人類學家,剛開始其實是不太適應原促會非常「經濟」(或「不經濟」?)的工作模式。開很久的車才到部落,一坐下就談計畫,談完便離開趕往下個工作點,如此蜻蜓點水的行程,實在很難與族人建立關係,或對部落有較多的��瞭解,尤其我有教職無法全程參與計畫,更增加了想要深入認識的難度。為了讓這些點狀的接觸能夠有生命力地擴張為線、面,進而⻑成讓理解和行動得以支撐的脈絡,我盡可能地撥出時間參與計畫中原本不歸我職責的各項活動,以此來累積所知、建立人脈;此外,當惠雯與族人、隨行的各領域專家談計畫時,我一定專心聆聽,並且不時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抓著惠雯或原促會其他成員聊與計畫相關的人、事、物。
從評鑑委員、陪伴顧問,最後變身為活力部落北區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透過這些年的參與和累積,我漸漸能較為全貌地理解當代原住⺠部落所面臨的一些發展契機與困境,並且進一步跨出計畫之外,抓住每一段旅程中所遇到的機會和資訊,去參與原住⺠社會相關的各種人際網絡和活動。
這就是為何大家會在臉書上看到我到處趴趴走,出現在這麼多部落的原因。僅管有許多時候只是短暫停留,但走過越多部落,我越深刻體認到台灣原住⺠社會的豐富多元而不敢聲稱自己很懂原住⺠。部落有著如此多樣性的原因不僅僅是因著「族」之間的差異,還源於被地理環境、周遭互動之族群,歷史過程等種種複雜交錯的力量所形塑。永遠記得那年跟著朋友隨族人坐著流籠進到霧台鄉大武部落,看到土地裡⻑著如此多樣的傳統作物時有多麼的驚訝,過往的部落經驗讓我以為如此景象是早已消逝只存在於文獻的美好文化與傳統,事實不然。
然而,當驚豔於台灣原住民文化多樣豐富的同時,這些年走進不同部落映入眼簾的,卻又往往是入口意象、花台、故事牆等各種類似的設置,��內容也大同小異的往往是狩獵、織布、穀倉、瞭望臺,或穿著族服的巨大人形塑像。這些原本用來表徵自我族群特性的「不一樣」變得越來越「一樣」,尤其是經過各種類似「活力部落」這樣的計畫大力塑模之後。「觀光客的凝視」和「計畫評鑑的指標」已經內化,進而形塑了許多族人們對於部落應是什麼模樣的標準想像,以致於「我們這裡看起來不像原住民的部落」或「我們部落沒有文化」成為不少族人對自己部落的負面評價。
我開始思索身為一個人類學家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究竟什麼是傳統?什麼是文化?在參與活力計畫的過程中,對於這兩個如此關鍵的詞彙,我看到政府單位的「操作定義」、族人的認知、學者的想像在其間相互競逐、妥協或複製。拆解這些糾葛線團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有能力成為其中不同領域的「文化轉譯者」,同時也嘗試在體制中提出質疑、作一些翻轉,或者修正自己原有的想法。
去年我所陪伴的嘎色鬧部落就讓我體驗了一場「文化」震撼。在選擇營造「部落意象」時,嘎色鬧的族人沒有被所謂的「族群」文化所綁架,而是找到了「蜻蜓」---這個他们有著共同兒時記憶,因此可以投注情感與意義的物,作為代表部落的象徵,而後將其轉化為具體部落意象的過程中,又透過共同的討論與行動,賦予「蜻蜓」這個原本可能日漸從記憶中被淡忘的「物」新的詮釋與意義,使其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媒介。
「為何是蜻蜓?這和泰雅文化有何關連?」,從開始的不解到最後的讚賞,嘎色鬧族人將蜻蜓逐步建構為共有部落意象的��過程,讓我重新思考什麼是文化,以及所謂的「傳統」和「文化」在當代部落營造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是我這些年來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過程中,常常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嘎色鬧的「蜻蜓」入口意象

族人協力構思、製作蜻蜓意象
未完待續
當年和部落的關係不是從「研究」起始,因而種下了「不專情」的基因。這些年來之所以如此用力地抓住機會到處走部落,一開始是希望能瞭解當代原住⺠社會的現況、需求與想望,藉此逐步厚實自己「回饋」部落的基礎與動能。如此「功利」的出發點,卻意料之外地獲得了許多知識上和情感上的反饋。我必須坦承目前能花在人類學學術研究的時間非常有限,但是這並不讓我覺得自己遠離了人類學,反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讓它入心、入身、入魂。
人類學本就是浸淫在生活之中,關注日常細節的一門學科。當它已經成為我視角與行動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時,不論是經由芭樂人類學的部落格書寫、日常生活的臉書po文、公務人員培訓的演講、活力部落,或是目前我投注最多心力的原住⺠專班,我一方面透過言語和行動向不同人群介紹、交流什麼是人類學,同時在一趟又一趟遇見他者的旅程中思索人類學的本質和特性,並咀嚼它帶給我的種種平凡又深奧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