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現生動物學與動物考古學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朱有田|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副教授
臺灣位於亞洲大陸的最東邊,島上許多動物經歷多次冰河時期,隨著陸橋的出現與消失,加上晚近人類遷徙等因素,導致物種的隔離分化、交流,甚或因人類行為而滅絕。動物考古學(Zooarchaeology)的研究,可以提供過去臺灣野生動物與人類及自然環境互動的證據。當今,分子生物技術學、生物資訊學、動物形態學(Zoomorphology)、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的進步,也促使現今動物考古學必須與這些科學緊緊結合,以獲得更精確的研究結果,得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檢視過去與現在動物相的變化,以探究氣候變遷對於動物演化的影響、或人類馴化對動物性能與形態的改變影響,甚至不同物種間的遷徙與雜交的轉變。臺灣雖然是個小島,但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地質性質(陡峭高山的地理隔離與豐富氣候類型),符合做為上述研究的條件。既然條件如此優渥,為何迄今臺灣動物考古學的研究仍無法獲得明顯進展?欠缺現今生物學、考古學與化學領域的��整合,缺乏紮實完整的動物基礎資料庫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現代生物技術與考古動物學
過去,生物學家進行動物分類時,多以地理分布、外觀形態、骨骼形態、生殖、行為、食性或棲地選擇等特徵,做為分類的基礎。由於這些特徵易受環境影響,且量測與定量上較困難,運用在某些物種的分類上仍有爭議。1953年Watson與Crick兩位學者證實DNA為雙股螺旋結構後,DNA的複製與在遺傳演化上的機制與地位才被瞭解。1965年,Zuckerkandl and Pauling提出DNA與分子鐘(molecular clock)的概念:DNA或胺基酸序列會隨著演化而進行突變,因此這些突變的DNA可以作為內建之生物時鐘,記錄生物過去的演化事件。DNA非常穩定,亦不會受環境影響而改變核苷酸序列;再者,利用DNA遺傳密碼作為親緣關係(phylogeny)分類或演化依據,常以核苷酸序列或以對偶基因座(locus)上之對偶基因(allele)頻率與基因型頻率(genotype)為計算依據,故量化上較明確,所得到的數據可經由計算統計得到較明確的結果。但利用DNA資訊進行現生動物或遺址出土動物遺留的研究真的是無往不利嗎?本文藉由幾個獲得遺址出土動物遺留中DNA資訊之技術原理來探討這些研究的困境與學術整合的重要性。
獲得遺址出土動物遺留DNA:從遺址出土動物遺留獲得DNA的研究中,以選擇及判斷樣本保存狀況為優先步驟,考慮因素包括樣本所在環境、樣本完整性、樣本是否已碳化?有無受微生物破壞?等�等客觀因素。通常,牙齒因有珐瑯質保護,長骨外層緻密骨(compact bone)組織緊密,較不易被微生物侵入而破壞,保存完整DNA的可能性較高,因此常以這兩種生物遺留為抽取DNA的優先物件。然而臺灣環境潮濕,許多遺址靠近海邊,樣本含鹽量高,不利於抽取純化古代DNA(ancient DNA)。得到候選樣本後,須先以去離子水清洗,然後在密閉負壓環境中,用牙醫電鑽(drill)鑽取骨頭內骨粉(如圖ㄧ),再以蛋白酶(protease)與清潔劑(detergent)去除骨粉中蛋白質與脂肪,後以酚及氯仿(phenol/chloroform)純化,進一步去除蛋白質,最後以酒精濃縮沈澱DNA。
遺址出土特定DNA的擴增:由於遺址出土DNA含量少,且大都已被破壞,導致片段化(fragment)。因此須經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擴增(amplify)。PCR反應須加入遺址出土DNA(當作複製模版)、熱穩定DNA聚合酶、四種核苷酸、一對引子(已知序列的短片段核苷酸,用以引導聚合酶進行專一性的特定DNA擴增)與緩衝液,然後經一系列程序化升溫與降溫完成擴增反應。所得經擴增的PCR產物再經序列分析(sequencing),即可得到DNA資訊(圖二)。但由於遺址出土DNA含量少、雜質多,不易被擴增,所以過程中必須使用效率相當好的聚合酶,且獲得之增長片段短(每次約100-300個核苷酸)。以目前我們研究室的經驗,分析距今100年內的樣本成功率約為90%、500年內約60%,而2000年內則降低至30%以下。因此分析遺址出土DNA序列是相當具挫折且昂貴的研究。
現生動物學DNA資訊對於獲得古代DNA的重要性:由於動物演化具有連續性,因此遺址出土動物遺留的DNA資訊對於詮釋現生臺灣動物遷徙與演化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從遺址中獲得出土動物遺留DNA資訊的第三個重要工作即是“比對”。然而,由於擴增遺址出土動物古代DNA的困難度高,除前述因素外,另一個重點是必須對所擴增的DNA序列在該動物族群的多型性(DNA polymorphism)有一定程度瞭解,才可以設計出合適的引子,用來擴增特定DNA。綜合上述因素,在進行古代DNA研究前,首先必須建立現生動物特定DNA的檢測與技術平台,還有對該現生動物之特定DNA序列多型性也必須建立資料庫(gene bank)。亦即,檢測與建立現生動物之基礎族群遺傳資訊研究是進入古代動物DNA研究的必需要件。有了這些基礎,才能增加遺址出土動物古代DNA序列的研究效率。而獲得考古遺址動物遺留與現生特定動物分子遺傳的連續性資料後,再結合氣候、植被與地理資訊,才能獲得更紮實的研究結果。
DNA的分子遺傳研究可以完全取代傳統的動物分類方法嗎?通常分子演化研究皆以粒線體DNA或細胞核中少數DNA或基因序列進行擴增,再根據其序列多型性進行統計與分群。因此,綜合少量DNA的多樣性資訊來解釋多基因效應(polygene effect)所造成的整體特定動物遺傳分化,甚至人類對動物馴化所造成動物形態及性能上的差異(如骨骼形態、毛色樣式或棲地利用等等),邏輯上會有問題。因為,以現今少量DNA的分子遺傳資料並無法完全精確反應出過去物種所有的遺傳分化;另外,臺灣是海島氣候,潮濕炎熱,許多遺址接近海邊,鹽與其他離子成分高,因此遺址出土之動物遺留通常保存狀況並不好,造成在進行古代DNA的聚合酶鏈鎖反應時成功率並不高。要從遺址中獲得完整DNA資訊,並不容易。於是,整合骨骼形態量測學��(Osteometrics)、顱骨形態量測學(Craniometric)與分子遺傳技術,在遺址出土動物的分類研究上,變成不可或缺的趨勢(圖三)。但臺灣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留除了狗外,其他動物如野豬、鹿科動物或其他小型食肉目動物的骨骼樣本,常因樣本經擾動而破損不完全,判別與比對上增顯困難。因此,現生動物的骨骼形態量測技術平臺、特定動物骨骼形態量測資料庫與數位化圖檔的建立亦不可或缺。唯臺灣在過去與現在,無論在動物科學領域(如生命科學系或動物科技系)、動物考古領域或是博物館,皆缺乏有系統的收集現生動物的骨骼、遺傳樣本,亦缺乏具備古代DNA分析與骨骼形態量測技術的專精研究人員。
就如這文章的標題:當臺灣現生動物學與動物考古學走在不同道路上,代表臺灣的現生動物學與動物考古學研究無法深耕,因此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整合是相當迫切的。均衡的基礎動物科學訓練、有系統的樣本蒐集、加上分子生物技術或現代量測技術的建立、資料庫建立與培育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是學術單位與研究單位必須儘快面對,而政府在計劃經費上的支持更是責無旁貸。

圖一、利用牙醫用鑽頭鑽取遺址出土鹿科動物下顎牙齒骨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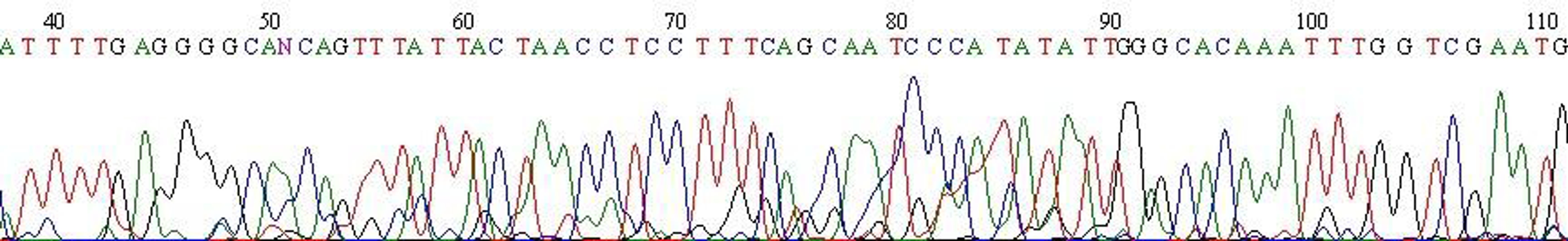
圖二、淇武蘭考古遺址出土鹿科動物粒線體細胞色素B(cytochrome b)DNA經萃取純化、PCR反應後,所的到的部分DNA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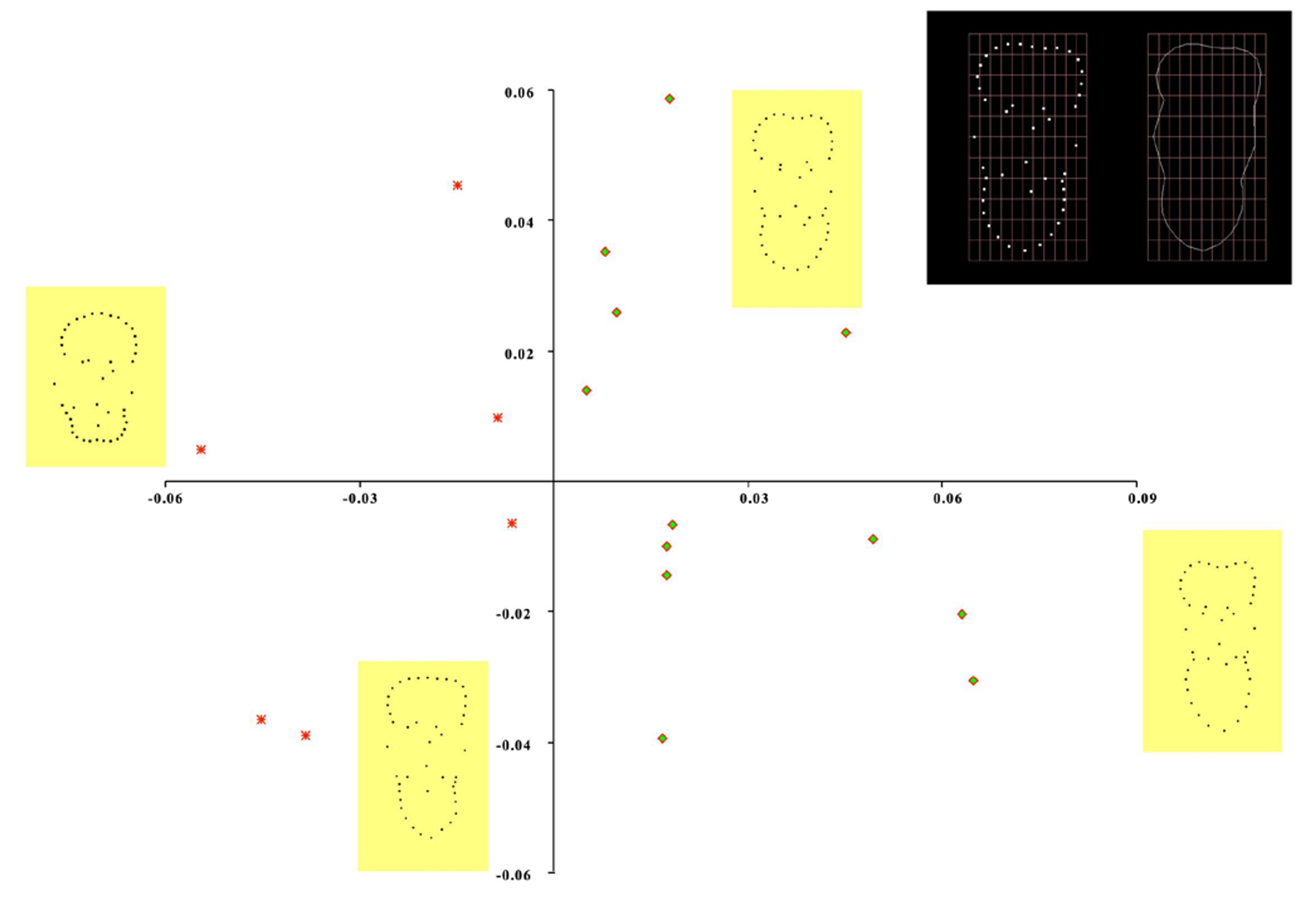
圖三、利用臼齒上43個量測點進行臺灣野豬(左、綠點)與蘭嶼豬(家豬、右、紅點)的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分析,右上角縮圖為量測實例。
